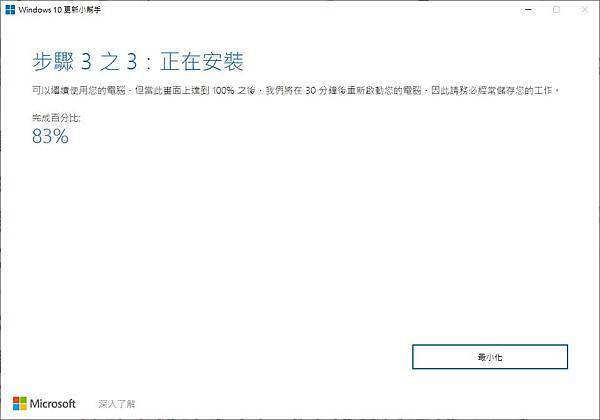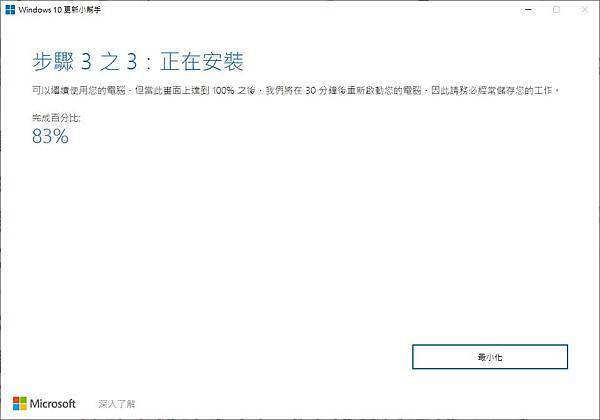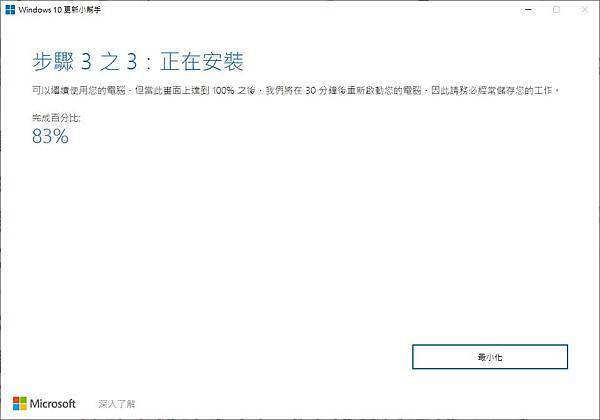
TL;DR: 重灌 Windows 是最好的選擇。
大概是 4 月初看到新聞,說微軟即將不再支援舊的 Windows 10 版本,並會開始自動透過 Windows Update 推送新的版本給使用者。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3,600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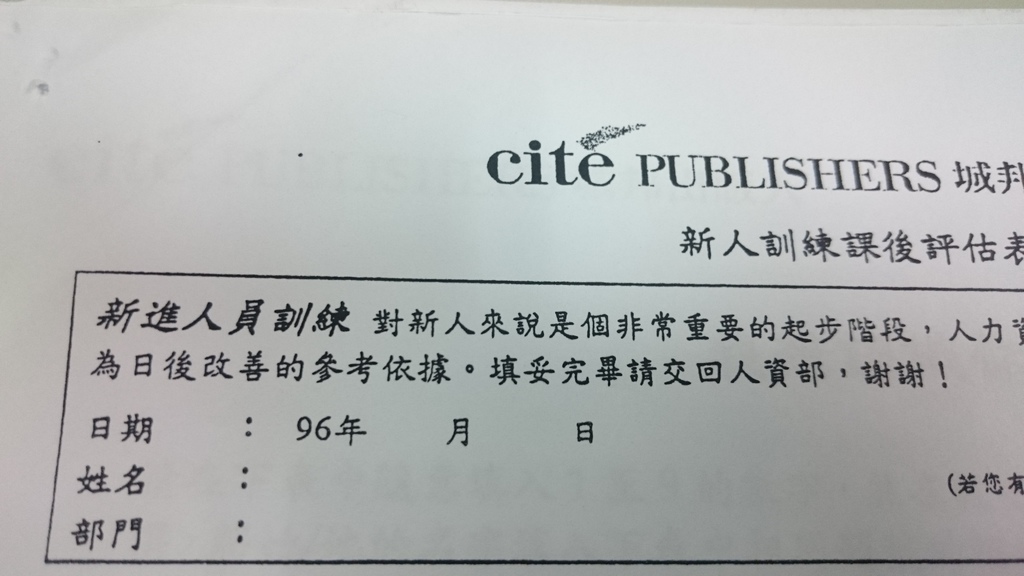
1/24
台北測得最低 4℃ ,各種沒想過的地方下起雪啊霰啊霜的。所以世界末日要來了嗎?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32)
9/18, D-30
有些人的見面頻率開始以五年十年為單位,有點可怕…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46)

8/31, D-48
撒唷那拉 你向我 say goodbye 沒情就撒唷那拉 有情再擱來 人情世事 惦惦看在眼內 過去的錯誤 全部抹一抹重來 撒唷那拉 你向我 say goodbye 沒情就撒唷那拉 有情再擱來 運命好歹 我卡會知 心內的痛苦 一嘴吞腹內 啦…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34)
07/29終於到了可以暫時喘息的休假。從去年十一月開始經手這個亂七八糟殘破不堪的案子,到現在剛好是八個月,真是名符其實的「無盡的八月」啊…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16)

06/10兵疲馬困,何時才能休養生息?
06/06 去了一趟三創,每層都繞了一次,很多體驗區想設法讓你掏錢買單,但是買東西還是去隔壁的原價屋買…大概只有四大門市的手機區人潮比較固定。至於隔壁的光華新天地,根本不用擔心有人搶你的生意吧,因為根本就不會進去了啊…以前鐵皮屋時代和橋下時代都好逛多了…06/012G 手機對我來說只剩下鬧鐘和收簡訊的功能,偶爾會有詐騙集團和催銷電話迷路打進來; 3G 手機辦來也只是拿來刷 facebook 和 instagram ,偶爾出去玩迷路時用一下 google map 、打打卡、傳個照片到 IG 上。 line 充滿了親戚們轉貼的內容農場的無聊訊息,已經快要懶得開了; slack 和 hipchat 都是拿來收公事用的,一離開辦公室幾乎也是沒什麼用;有時候還會有 facebook messenger 來的訊息,畢竟它還是台灣社交平台的大宗;至於被微軟買走的 skype ,好像只剩下每天登入的功能了…。健康檢查的報告出爐了,恐怖的紅字早就在預料之中,自己也很清楚;從這個案子開始到現在,已經不曉得半夜醒來多少次、失眠又多少次了,甚至連健康檢查前一天晚上也是失眠,又怎麼可能會有好的結果…。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64)
05/16
搶票心得:動線設計有夠糟…
據說開賣前 N 分鐘網站就流量管制中了(我還以為只有 ibon 有這個選項)
明明票價只有一個選項,為了不存在的信用卡優惠,還要用下拉式選單(對,我一直忘了選這個)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38)
03/21
到底要因為這件事失眠多少天?
03/15
國中同學會。很多同學都還以為我還在上一份工作,多久沒見到大家了?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46)
很久沒有時間整理部落格了…
把站內訂閱 RSS 的改用新的動態訂閱功能去訂,整個 RSS 只剩下站外的了
把參加活動產生的自訂欄位看了一遍,過期的活動也刪掉了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29)
總覺得今年沒來由的過得很快。
今年對自己意義最大的應該算是一個人跑去環島這件事了。
明年應該也會安排一趟長途旅行,適時的放假真的很重要!以前都不會覺得放假是件重要的事…
repeat ❤️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2) 人氣(152)